耳闻目睹的麻风病
| | 发布日期:2012年06月05日 来源:春秋农事 原创作者:拾穗居士 点击数: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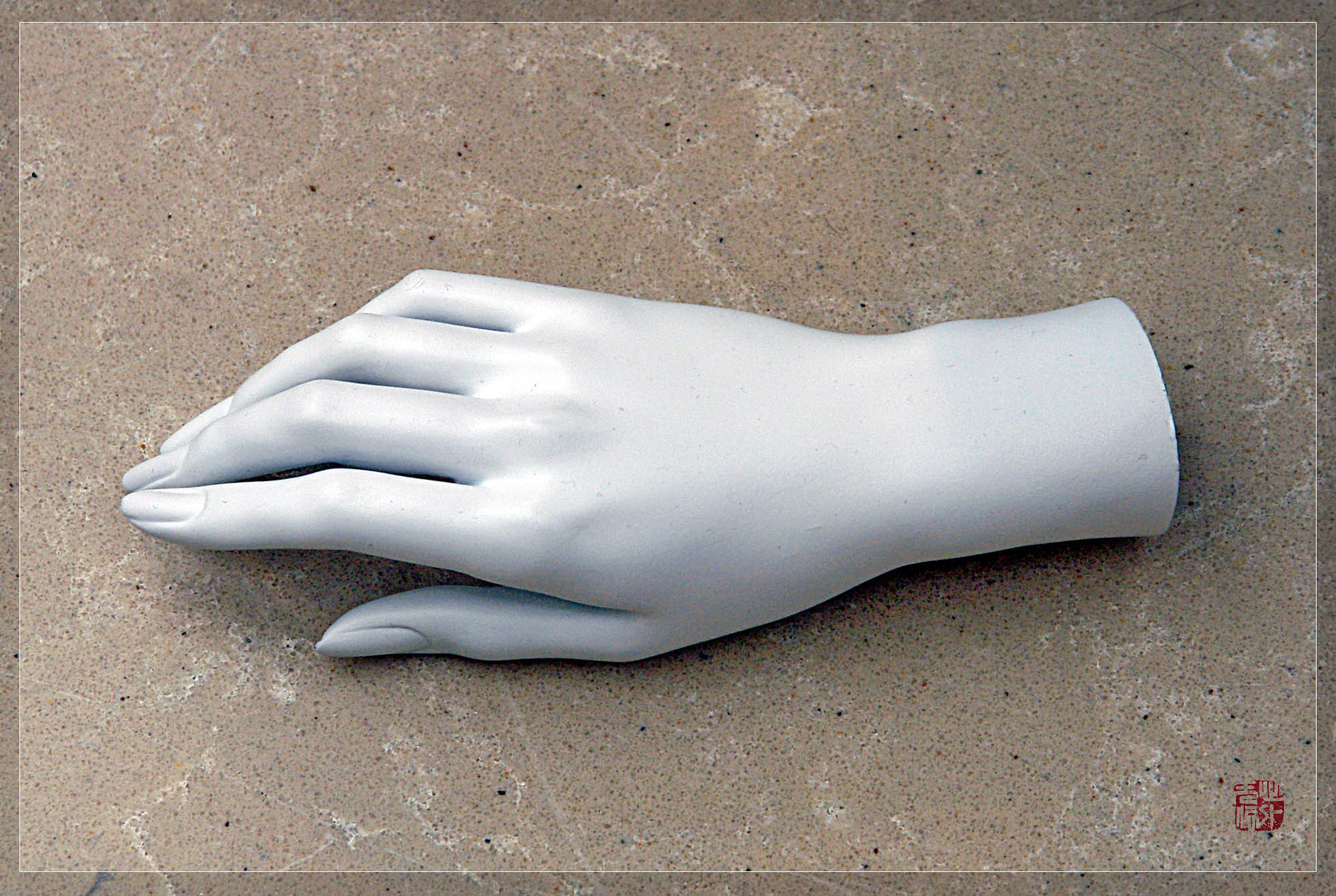
我在幼年时,就听说过“固箩”,懵懵懂懂知道它是一种“生病”。
“固箩”,福州方言,就是普通话说的“麻风”。
然而,到今天,我也不晓得麻风病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得的,怎么传染的,大约知道患者的手指只能弯曲,不能伸直;脸部的什么器官——例如鼻子,会溃烂;他们被隔离到别处,不能与家人一起生活;他们会死亡。
能够知道这么一点,完全是听我的父亲无数次说到“固箩”,还有我下放到农村时的一次恐惧感,再就是看过一部电影。
我从不去查询“麻风”。要想了解,实在只是举手之劳。但是,一反所有的积极求知欲,没有去查,连个念头都不曾有过。
原因?
不清楚。
或许,有我的父亲在担心,在提醒,在预防,我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父亲一辈子都在向家人问同一个问题:“这衣服干了吗?”然后不无担心地嘟噜一句:“不干的衣服,穿了会固箩啊!”
只有得到明确的答复:“肯定都干透了,安安心哦!”然后,才会回个笑脸。
除了酷暑,这样的对话要少许多,其它的季节,不但必定要走过场如此对话,还得在梅雨的春季,当面烘了,才休止追究的。
我的母亲面对几乎天天都有的这问话,大多数时候都简短轻应之:“干了!”便罢。却也有极不耐烦的例子:“跟你说‘干了!’你还不相信!你要我怎么办!要我叫日头再出来!特意来照你这衣裳!” 在这情况下,我的父亲一定赔起好些笑脸:“好!好!好!干了就好。”
我的母亲谢世之后,我们晚辈的谁还敢顶撞,只能是耐心重复:“爹就放心吧!”“翁!保证都干了的!”
我的父亲一辈子的担心,一辈子的同一个问题,到一辈子结束了,也并没出现。这是担心的结果?是不成问题的结局?还是根本就不是麻风病的病因?因为我不知道麻风病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些,就此可以了结。
我的父亲还认为,人不能趴在桌面上睡觉,因为这是一定会得“固箩”的。
因此,我在上小学时,无数次要在老师的命令和家长的警告之中选择,必须在老师中午来教室检查时,赶快地双臂弯曲交叉,把头拷在手臂上,闭紧眼睛,等老师离开,再放下手臂,偷偷玩自己的东西。
这样的异动,常常被小同学们取笑。
还好,没有谁向老师报告。
于是,在老师看来,我是遵守纪律的好学生,在我的父亲心里,我是他的乖乖囝。
所幸,我不曾因此成为两面派,人格也未被导致分裂。

1968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三年,10月,省直机关的干部开始被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刚去时,因为生活尚未安定,所以由大队给我们“派饭”——大队革命委员会的会计列出一些贫下中农的名单,交给通讯员,通讯员每天把我们带到名单上的一户人家去,我们交定量的粮票和三角钱,就有三餐的吃食。逐日轮流。
有一日,我们三人吃过早饭,才回到大队部,通讯员就告诉我们,中饭和晚饭都不再在刚去的那家吃了。经我们再三问过,才知道“那一家有麻风病。”
恐怖突袭而至!
措手不及的我们,马上抠喉咙,竭力呕吐,猛烈刷牙,用大量的肥皂洗脸部,还用刷子刷洗其它所有暴露的皮肤部位,以及换下的衣裤。除此,便是面面相觑。
还好,什么也没有发生。
当我们一年、二年、三年先后离开那里时,那天的恐惧已忘乎曾经。
所以,现在,我来写这段往事,还觉得对不起那户人家,他们特意为我们“城里来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干部”煮的木薯米汤,捞的白米饭,那心,那情,还有他们知道不再去吃他们家做的饭时,他们在想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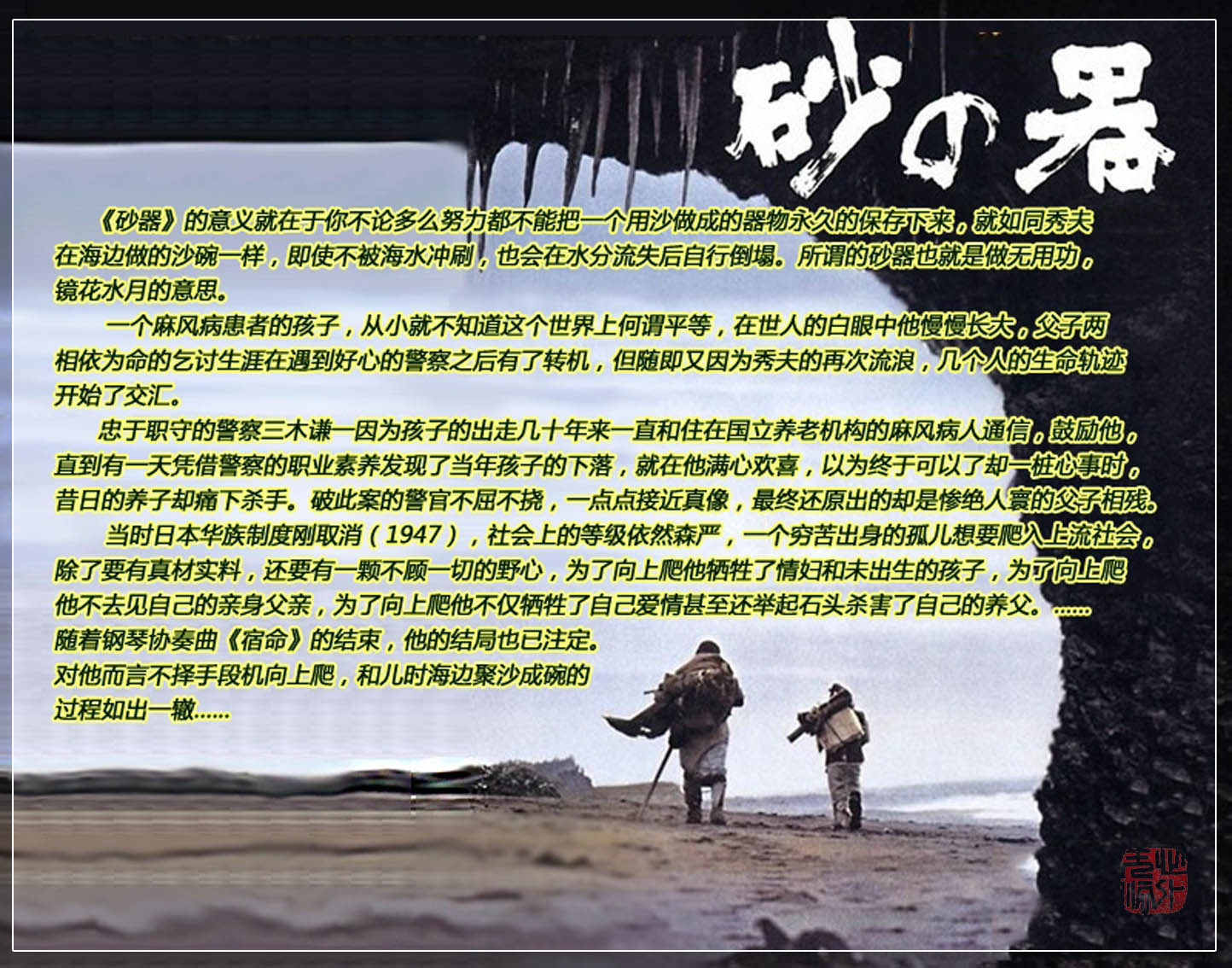
我第一次看到麻风病患者的相貌,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看日本电影《砂器》时见到的。作曲家和贺英良的钢琴曲作品《宿命》和他的杀人的事,我已经模糊,但他的生父本浦千代吉是个麻风病人,印象还有。
如果把本浦千代吉过去带着年幼的儿子本浦秀夫一起流离失所,一同遭遇的情景,以及老年的他在国立疗养院,看到警事厅侦探带来的和贺英良的照片,凄声痛哭,那一幕,与片头——海边沙滩上,孩子堆沙成器,沙土都被风吹散去,那场景,联系起来,我总感觉,人心啊,有一种病痛,远比麻风病更可怕。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哪些人会得,只知道患者的心灵只能被扭曲,不能伸张,甚至巴不得去死。
2012-06-04 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