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老王蛮可怜的
| | 发布日期:2011年05月04日 来源:春秋农事 原创作者:拾穗居士 点击数: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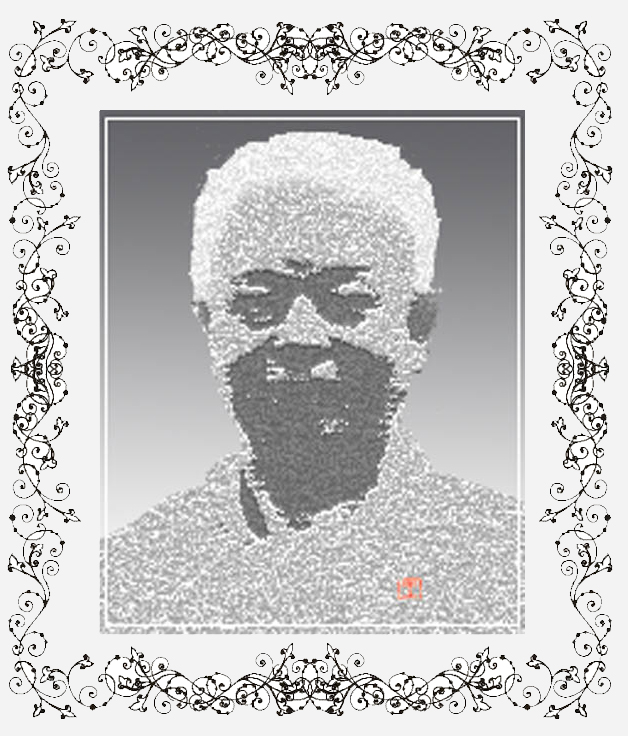
我们单位的人,在非正式场合,相互之间是不以职务、头衔称呼的。老的叫“老”,小的叫“小”,中的直呼姓名。
我们当面尊称他“王老师”,背地里叫他的姓名,没叫“老王”。
其实他颇具王者的派头。圆圆的大头,圆圆的大脸,身材矮矮着圆圆的,才六十,雪白雪白的板儿寸,小小中中的老年斑。笑起来,活弥勒。
他并不常、但总会不失时机地说明他为王的过去。我能记得起的,也是他最重视的有三点:任过地委专署党报的负责人,以负责人的身份陪同某领导视察自己所在的单位,在省级学术期刊当负责人。到来领导我们这个部门工作的时候,上级下的任命文件上写明的也还是“负责人”。这一次的原因是他的年龄超过了正处级的上限。但无论如何,他是我们的头。
我们这个部门最少的时候,只有两个人,最多的时候今天来了第五位,三天内一定会有一个人调走,总共保持着四个人,编制是六名。人是负责人老王要来的,或者经过他同意调进来的,怎么来一个又走一个呢?走的不是停薪留职下海去了,就是攀上省政府哪个部门升了,再嘛到北大读博了。得!这风水转来转去的,不移不动不变的就老王和我。
大家直呼我姓名。
老王是典型得很很很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有一类型知识分子的典型——以特有的不可指责的但能让人觉察得到内涵的语言,向对自己有厉害关系的官员和名家附会,这是“清”;不怎么露脸的,但骨髓里瞧不起不如自己的人,是谓“高”。但要公开的阿谀,或公然的鄙视,这类人又都不做的。正是这样的可为和不可为,这类型知识分子的“等级”意识特别在意。当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特别捍卫自己的观点,在争论的过程中,一旦坚持己见得严重时,也会忘我,因为忘我而置“等级”于不顾。
正因为我看明白了老王,所以我跟着老王工作的时间最长,与其说我最顺从他的旨意,不如说我认为他从来不损人利己,仅仅是保护自己,甚至更多的时候,他会利己利人。在这样的社会里,这样子的老王们之存在,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跟着王老师做课题研究,他在实际现场的理论或操作虽然不怎么样,但他写起论文来一丝不苟的那态度,别人什么感觉不知道,我是肃然起敬的。关于这一点,我今天才说。如果那时候说了,我在它的心目中,一定更好。
我是一直保持着我自己的这样。
老王组织了一批相关单位的头面人物,顺理成章申请获准成立了我们学科的省级学会,让我筹备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我同着俩“小“的,从写信封到发函,从跑邮局到布置会场, 从倒开水到糊个投票箱,无一不让我们的王老师他老人家眉开眼笑。我们累得半死。
会议结束,老王有了个正式的身份:会长。
我经他提名,被选为秘书长。
秘书长做什么的?写信封、发函件、登记论文、与作者商谈、编辑一审、送副会长二审、会长终审、合集出版内部交流的出版物。
对于有正式职业,领一份正式工资的老王,这是他的成就,最重要的是他终于是“长”了,有一枚公章。凡是有做派的首长,是不自己锁住公章的,都是交由秘书报告,王会长把那物件交了给我。而对于我来说,则是额外的大负担。
老王还做了一件大好事,那就是在我们这办了一个北京大学某某系牵头下的、冠以“中国”二字的某学科函授大学的省级辅导站。老王理所当然的有了第二个正式是身份:站长。
这是有一定酬劳的。
因为有课任,可以教书,可以批考卷,可以改论文,所以有课时报酬,有阅卷费和改论文费,我是相当得实惠者之一。按老王对我说的:“这样,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你的家庭生活啊!”
我笑笑。
老王不了解我。
三年后,根据教育部门的文件,这所函授大学在一批被取消的名单之列。善后处理的事,老王作了指示,由我负责!
老王认为他比我们单位其他人多更了解我。所以他这么向他人推介我:“把事情交给某某,如果他答应下来,你们就不用担心,也不要去催他,到时间,他给你们的一定让人满意。”
有一天,老王很高兴地告诉我:“我们这个部门有一个秘书的编制,我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所以,我已经报给人事处了。”
我笑而坚决地谢绝了王老师的好意。
他脸一沉:“为什么?这是个机会啊!秘书是正科级啊!”甚至他还三次要我说个理由给他听。
我不得不说:“王老师,如果要当官,……”
老王这下子似乎开始了解起了我。
尽管如此,我仍然怀着感谢的心情,感谢有长辈能利于我。
那时我已年过不惑。
年至六旬的老王,对改革开放既热切,又保守。
在石狮做课题调查时,我们与当地的多家私企的老板开座谈会,王老师的发言,每次都克制不住对私企发财的兴趣和向往,有时,他也点名要我发言。我说的说,提问征求答案的多。老王会后要求“小”的们向我学习,正派、稳重、谦逊,是个做学问的人。
但有一次,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参观而奇想感发,我在会上说:“我发现,性成熟年龄的女性,一个月来一次经期,一次四五天,如果发明纸质的,可以随换随丢的,那多好,也不用现在这样的橡皮的。妇女的人口数量那么大,市场应该非常看好的。”
会后,我才发现老王的脸像被我抹了一把灰。晚上他找我单独谈话:“你知道嘛!你的想法很下流!我们目的是来做调查研究的,你怎么可以去看那个,还敢这样想!……”
直到几年后,全国第一批纸质妇女卫生巾产品上市,报纸有新闻报道,一听厂家是石狮的一家民企,我才终于为我的邪念而自豪——不管是不是我的想法对谁有启发,但事实证明我聪明属先锋正确。“小”的们说,“那时候,要知道我们几个人集资办厂,不就发了?”
然而,这时候,善良的老王却已猝死。他死在我们单位党组织的一场会议上。他发言时,支持学生,越说越激动,后来口齿不清,紧接着突然倒下……抢救无效。这天,1989年的入冬,会议的内容关于这一年夏天。
1990年,我们单位的头一次性任免了好几个。那以后,凡有职务、头衔的,相互之间的称呼一般随之而用。
记得老王的讣告上,他的正式身份是“负责人”和“会长”。
2011-0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