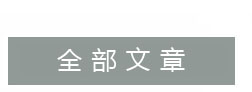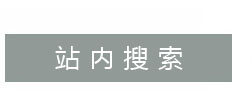(接上篇 http://www.cqns1946.com/contents/7/1308.html )
故事七 种竹

埋鞭岁首立春前, 夏至欣然节节鲜。
韵律高低因雨醒, 风情枝叶枕云眠。
蝉衣堕落三秋地, 寿石扶摇四季天。
郑燮糊涂苏轼醒, 东坡食竹板桥怜。
接下来,很自然地,故事延续到“种竹”。
年前属冬季,天寒地冻的,“他”已经刨开成年竹的根,从中剁下一小截一小截有似芽尖的竹之“雄性生殖器官”,然后埋在湖石之旁。经过春雨,经过惊蛰,经过春分等等,到夏至,竹鞭雄起,破土成长。“他”因此想到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更加自“醒”,也因为扎根,以使“荒居”有了全新的生机。
“他”的“醒”,既有大自然“雨”的作用,也有画家与词人的感悟,即:郑板桥对竹的爱怜跟苏轼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如果故事七只在讲“他”怎么样种竹,竹子长成什么样子,那没什么意思,讲给小孩子听听都打瞌睡。但是,因为来了两个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人,而且尽人皆知的两大名人,故事就变的幽默了。
幽默不同于笑话:笑话是拿别人取笑,幽默是自己拿自己开涮,说苏东坡不也被贬谪得比潇湘更远的岭南嘛!郑板桥要是在世,能画出我这样的竹吗?
七故事显得平,显得和,显得安,是五、六里“他”故事的跌宕之后,顺应成章的。
故事八 画树

平林仅写树三三, 破墨多些青与蓝。
淡湿干浓相得意, 沉凝毅炼各当担。
前承厚土心中出, 后揽凉风纸里含。
八大山人之哭笑, 今无学者论头簪。
“他”在故事七的“种竹”并不尽兴,毕竟有过官宦仕途的生涯,有文人盛夏绘春的山水情怀,于是,“他”再次提笔。
这次,“他”继故事七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临”了“扬州八怪”的又一个之一“八大山人”朱耷的树木画。
八大山人落款时的题名,虽然可看作“哭之”,也可视成“笑之”,但这都不是“他”要借喻的重点,“他”的重点在于“当今”已无学者去讨论朱耷的削发为僧,后来为什么又盘发横簪改道炼丹的人生。
这时,故事讲的话题出现了哲学要紧的“信仰”。
“他”没有因为种竹尽兴,也没有由于画树释怀,于是,他又走出宅门。
故事九 泊舟

行程过到未名州, 遣使船家酒肆求。
举箸闲情归脑后, 干杯快乐坐潮头。
赏心夕水轻轻载, 悦目芦花慢慢浮。
寂寞今宵还在此, 孤灯兴许引双鸥。
故事九是“他”走出宅门之后坐船。
没有讲要去哪里,要去干什么,只是讲:船在黄昏之时,停泊在一个连名都没的水中陆地。故事除了“他”的孤单感和借托于水、花、鸟的外景和内在的灯,别无新意。
注意,这时的季节已有芦花飘零。
因此有意思的,一连串的故事在“画树”之后,故事有了承上启下的转折。
但是——但是的但是啊,故事出现了一种心情无可泊,魂魄无处安的状态!
这状态本是极端无奈、再也没有可以比拟的无助,我竟然用“闲情”、“快乐”、“赏心”、“悦目”这样的词语来讲出。
因为在讲述这一状态时,我联系到了自己有时的就是这样。
故事十 餐色

夫尝嫩绿得时鲜, 蕨菜溪鱼可入筵。
举杖行吟生醉意, 闲情对景去愁眠。
心疑热辣红椒树, 怪异清凉碧玉天。
直到红枫凄楚了, 沉迷艳丽记春缘。
故事十,画面上草色的鲜嫩之绿,与左上方原题的“千树秋风万叶飞”季节,在我看来是极不协调的,不合季节色彩的写实逻辑的。所以,讲故事的我不得不编造出:“他”在出走之后,继水路再“举杖行吟”的陆路往前,就连“醉意”都延续了故事九的“遣使船家酒肆求”。在“他”的眼中,枫红成了朝天椒,碧云天成了无云有玉的乱象。已经深秋却又秀色可餐,使之回到故事二“盛夏”时的绘画春色春景。
这是什么心情?这是什么欲望?
讲故事的我,认定是“他”念念不忘要回到被“贬谪”之前的满目“春缘”,尤其是酒醒之后。
人啦,因后来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会十倍百倍地强烈欲望着重新得到,即使已无必要那东西。哪怕“他”再被召回原职,“他”无非:要么只是虚荣心的一种得意,要么就是变本加厉做比过去更猖狂的反扑。
在我讲“他”的故事里,季节一直是在恶暑,即使“他”有春游,但绝不可能有“春天的故事”。
故事十一 相对

身居恶暑热难当, 画面严冬枉挂墙。
望雪驱炎焉有用, 思梅止渴怎能凉。
常言自在非他在, 岂论冬装即夏装。
问答双骑前去意, 竟然羡煞火骄阳。
一连串的故事总数是十二个,第十一个故事要按古戏的规制,就是“压轴戏”——全本倒数的第二出。
要是全本戏,这已经是故事的最高潮。
“他”仍然处在酷热难当的时候。
“他”仍然在不实在的“画面”里煎熬。
“他”仍然处在一如永无止境地怕冷的希望夏天快来,怕热的眼巴巴大雪盈尺那样,自相矛盾地相对于现实和憧憬里。
可以很自得意趣地讲,第十一幅古画,能被我讲成画里二人相对“问答双骑前去意,竟然羡煞火骄阳”,而“他”“身居恶暑热难当”与“画面严冬枉挂墙”相对的,且唯我独!
故事十二 网秋

鲈鱼八月正肥时, 老父扳罾起兴之。
放任河塘秋夜月, 兜来草屋竹枝词。
凉风仗日攀枫树, 野菊扶岚醉竹篱。
怯问三年边戍事, 船家五子数盘棋。
这是大结局。
故事的“他”,已经彻底接受了“荒居”的事实,已经不再对官复原职寄望,已经学会了最简便的生活方式,甚至会捕鱼。
因为社稷起了多年的战事——连“他”的年纪已经不青的儿子,都被征走了“三年”!
这才是他迁徙到“荒”村定“居”的最重要原因。也是“他”的同僚“三年罔顾”“抚琴”之失“乐”的根本。还是那位盲友叶落归根的空想。
为此,“他”的关注已不再是,也绝不可能是自己,而是超越岑参边寨诗作和旁观“三离”、“三别”杜甫,切身之魂牵梦萦是“他”自己的儿子——“边戍”“三年”无音讯,想问而怕听到不好的讯息……
“他”换了一种打听讯息的方法:和远道来的“船家”下棋。
至于“五子”是“他”“边戍”去的第“五子”,还是“五”个“儿子”;抑或围“棋”甚至“五子棋”,都不在讲故事人的话下。
我这么的讲,是因为作为大男人,作为经风雨见世面的老父,我自己总有在最遇见某事,继而生情时,而言它。
2016-07-27
【本篇有关】
荒居 http://www.cqns1946.com/contents/4/4514.html
盛夏 http://www.cqns1946.com/contents/4/4515.html
观瀑 http://www.cqns1946.com/contents/4/4516.html
听风 http://www.cqns1946.com/contents/4/4517.html
抚琴 http://www.cqns1946.com/contents/4/4518.html
闻笛 http://www.cqns1946.com/contents/4/4519.html
种竹 http://www.cqns1946.com/contents/4/4520.html
画树 http://www.cqns1946.com/contents/4/4521.html
泊舟 http://www.cqns1946.com/contents/4/4522.html
餐色 http://www.cqns1946.com/contents/4/4523.html
相对 http://www.cqns1946.com/contents/4/4524.html
网秋 http://www.cqns1946.com/contents/4/45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