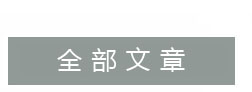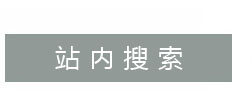荒居、盛夏、观瀑、听风、抚琴、闻笛、种竹、画树、泊舟、餐色、相对、网秋,一共十二首的七律,我写了十二天。
七律不但要有兴致,还得很要典雅的。兴不致,诗不起,而雅不典,斯文则七绝可矣。七律的斯文,还有种种别于其它语言表达形式的,此不赘言。
人多道“文学表达形式”,我何以曰“语言表达形式”呢?因为对我来实践,文学太斯文。学过,甚至痴迷顶礼过,最终还是不怎么会。语言么,口头语说的,写几行字句的,尚勉强;尤其日志,表达点什么的,还过得去。
所以,若一定要以文学样式的“斯文”来审阅,我六十岁以后格律过的所谓近体诗,粗鄙了。尤其这个月中旬以来的这十二天,更像讲故事,一天讲一回,一回一事。十二个故事;既可各个单独,也可以一连串起。
假若串起,故事总的有一个人物在其中贯穿。我希望“他”的活动集中在酷暑里,讲“他”怎么过日子的。篇名上个月就开始想,到现在还没有,不是冇想好,而是一个都没能想得出。
还好,十二个故事都讲完了。
少年时,因为受唐边寨诗人岑参的《逢入京使》,诗仙李白的《静夜思》,痛苦诗叟杜甫的“三离”、“三别”,乐天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等等诗作故事情节和人物形态的影响深刻,所以,今次我就想:现在这把年纪咯,能不能既不古风,又不绝句,还不五律,更要全都一种“七律平起首句押韵式”来讲故事。
诗是吟成的,用以唱诵的,对此我犯难,但又好之,于是,我学着模仿诗的形式,“讲”大白话。
试试吧!
故事一 荒居

峰峦叠嶂绝尘埃, 牧雨耕云日月来。
劲草包容饿虎啸, 清流洗刷躁蝉哀。
山垄不乏繁星卧, 瓦屋多亏巨石抬。
最使巡山心意满, 停留足迹雪皑皑。
讲故事,肯定首先要对故事的人物、其所在和基本的生活状态给于交代。这样,才好带动接下去的一连串活动,演绎出合乎逻辑的常态性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重点在说“荒”;怎么个样的“荒”。
为什么不是“荒凉”呢?因为现在的时令是三伏天,热的很。
那么,这么热的时候,当然就思想到凉快,所以,欲望想象冬天,而且有积雪的时候。
那么冷的天气,这个“他”为什么要出来走动啊?因为“巡山”。
什么是“巡山”?应该是为了打猎吧!要不前面的“虎啸”岂不白白铺垫了?
故事听起来,好像已经完整了。
其实,有一个问题没有交代。
什么问题呢?
问题是:为什么这个人要住到这么荒的一个地方来?是祖祖辈辈就居住在这里?还是因为什么、在哪年迁徙来这里?
故事二 盛夏

桃花绽放柳延伸, 浅草丘园绿隐嶙。
戴笠鞭牛犁旧地, 推舟击楫泛新津。
兴来熟悉偏迷路, 向往生疏要问人。
歇暑听蝉无处去, 悉心绢面画游春。
交代气候,是讲故事的人给故事里的人物安排“所在”时,给出的背景,带季节性的,有大自然气息的,有气候的。
标题已经很明确,“盛夏”。
然而,画面显然是春色春景。
如何摆平故事里的人——“他”现身在盛夏还是在春天,这是要讲好这个故事最难的难点。
故事之“讲”,得靠编。
要编的切题,要讲得合理、顺畅,一点都不别扭,才好。
我的讲法是:把人物的“现在”隐在画面之外,让在“盛夏”怕出门的“他”,在太热受不了的时候,宅着绘画。
画什么?画春时遇到的事。
什么事?游春,踏青,有人迷路了。
当时谁去?是独自去的,还是结伴去的?
如果是单个去的,那问路的应该是画里的白衣人。
倘若数人一起去的,那一围的人则是在问在地的白衣人。
无论是哪一种,白衣人都是“现在”正在绘画的“他”。
但从故事一的“荒”到这个故事的牛犁、舟楫、桃放、柳延、 绿草、丘园,背景的变换,个中的逻辑,总的来讲,都得由看官再去第二次创作。
接着故事一的问题,这个故事也存在一个问题:此人——“他”的身份、职业?
故事三 观瀑

如雷贯耳静喧嚣, 聚合分离论寂寥。
避死攸关因地界, 求生未必为天朝。
恭谦破碎从三叠, 傲慢流亡自九霄。
落魄安能如此水, 人间哪里不逍遥!
照第三个画面来推测,第二个故事去春游是肯定了的,“他”著的是白衣,目的是到“这里”来“聚合”,和几个友人、同道一起欣赏飞流。
盛夏观瀑,这是纳凉的好所在。
假如故事一、二,分别留下问题:“他”为什么要荒居和“他”的身份、职业是什么,那末,常服能着“白衣”者,其身份——至少曾经的身份——不会是黎民。黎民多半青衫黔布。
到故事三这里,讲到“避死”、“求生”、“天朝”、“流亡”、“九霄”、“ 落魄”,是不是对答案有所暗示了呢?
在讲故事的时候,问题的提出和所谓的暗示,叫做“楔”。如同写家们文法上的“伏笔”,章回小说篇末的“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故事四 听风

钱塘八月涌江潮, 倒海排山逐渐消。
但且姑苏行竹笛, 随时雨点滴芭蕉。
悠然感觉书翻页, 静谧知音马过桥。
莫苦盲人无色界, 推窗笑说叶飘飘。
前面的春游、观瀑,接下来的听风,乃至后面的抚琴、闻笛、种竹、画树、泊舟、餐色、相对,都在讲这个“他”的活动。一个故事一种活动,每种活动都在讲“他”的举止、所见所闻和内心反应。我设想,总应该在一个什么故事里,对“他”的“为什么”有个交底。
故事四为什么不是以视觉去看潮涨潮落,而是——而且都是——凭借听觉来感知风声?
因为是盲人。
既然是盲人,那故事二怎么还会绘画呢?
可想而知,这位盲人不是全部故事的主人公,而是一起春游的伙伴之一。
这样,故事的逻辑才具合理性。
盲人听觉中的风声,大势时如钱塘江农历八月十五到十七的大潮,贯通时如笛声中款款而行于姑苏美景里的游人,断续又似古代岭南音乐《雨打芭蕉》,轻到恰如书页的翻动几乎不觉,或许还因为风铃而联想到瘦马西风小桥。
这些讲来虽然是一个个形象的比喻,但又何尝不是故事里的故事呢——
伍子胥踏浪而来的怒气冲天。
姑苏游人中的许仙和白素贞。
还有“窗前谁种芭蕉树”、“伤心枕上三更雨”、“不惯起来听”的李清照。
再就是清翰林徐骏因“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的被问斩。
然后,马致远《秋思》的“断肠人在天涯”。
故事如果一直在讲一个人,一个明眼人,也许不如穿插一个不能看,只能听者,更加生动,也更能加深对最主要人物“他”的刻画。不是有一说法么:见汝好友,更知汝。
故事里套叠的这几个故事,有着共同的不安,一味的苦涩,盲人却最终乐观起来,因为内心能感觉到待得将来,可如落叶,归根而回。
“回”?
回哪里去?
问题还在出现。
故事五 抚琴

三年罔顾此弦空, 一任闲屏过竹篷。
隔着江山思社稷, 连同草木叹英雄。
朝廷总喜衣冠重, 病榻才知格律穷。
客座清风生指上, 无由却已入情中。
故事讲到第五,显出了人物曾身为朝廷命官,而且追求过职位的高升,然而迄今至少三年已不参政,乐不起来。
我如果就这个画面,把故事的“抚琴”完全导向正面琴操之人,那不仅必然落俗,还有不合乎从“荒居”到豪宅的突兀,难以讲清。
唯有把故事主角的“他”设置到侧座上,以“他”的手指轻微的举动,在画面上“反客为主”——与豪宅主人有着同样“隔着江山思社稷,连同草木叹英雄”的处境和情怀。
这样,二人手指动作的同步,“入情”就更比通常说的“知音”多了内涵,多了外形。
故事五的画面,人物的背景在庭园,靠雕石围栏的地方。
屏风上的江山篷船既遮住了“外面”的风景,又连接了院墙“里面”的人物。
是故,在一群游春、观瀑、听风之后,请个别到某人的府邸作客,人物的去留不但合理,还为“他”做客之后,辞别往下的活动作出过渡。
故事六 闻笛

江南曲笛近来声, 摆渡扁舟水面横。
浊暑支撑罗汉柳, 清波倒映鹧鸪行。
无琴有感焉能和, 有感无琴更绝情。
贬谪潇湘斑竹泪, 悠长古调悼京城。
出到豪门之外,“他”返回到自己的“荒居”。
某日,已经来到水榭纳凉的“他”,大概因为记起“上次”故事五的“无由”——没有实物——只能空弹,这下好了,故事六的“他”便叫家僮去把琴抱来。
正是这空挡之际,“他”听到并看见对面近处摆渡人的吹笛。
《鹧鸪行》原是潇湘古曲,表现鹧鸪展翅高飞的情景。又,古传说此鸟鸣叫之音犹如人语“行不得也,哥哥!”所以,故事讲到这里,“他”的被“贬谪”身份就露底了。
故事讲:“他”是从京城被“贬谪”到潇湘江南的。
“他”的袒胸和摆渡人的露臂,以及郁郁葱葱的罗汉柳,都与故事五画面左前方的荷花遥遥相映。可是,笛子的曲调即使吹的悠长高亢,在被“贬谪”的人听来,未必不是一种哀伤的悼念。
不管是悼念自己官宦仕途的结束,还是悼念故事五讲到的“社稷”之死,“他”的“琴”与“感”,在“他”的内心都难得和谐。
于是,他就吹笛想到湘妃因舜帝驾崩以涕汨挥,致使竹竿尽斑,见景生情自己的“悼”能有此力乎?!
(未完,转下篇 http://www.cqns1946.com/contents/7/1309.html )
2016-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