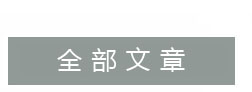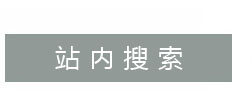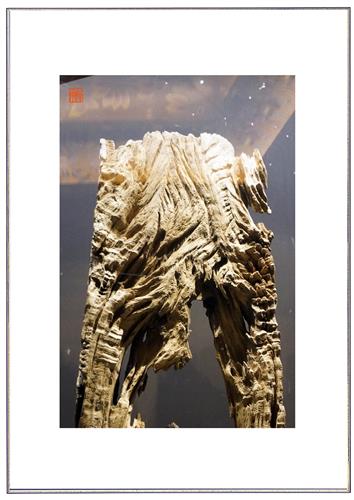
在我的内心里,我们家最安逸的年代,是1945到1965的那二十年。所在地,都在南平。住所则先在胜利街,租人家的房屋而居,直到1956年,父亲得了一间邮电局分配的家属宿舍,12平方米,于是,住所就搬到了梅峰坊16号。
之所以说最安逸,一是最先一段家里有祖母、父亲、母亲、姐和我,人很完整。
祖母随其高兴,有时会散步去五百米距的伯父家住几天。
父亲在邮电局上班,管仓库。父亲的职员身份体面,收入稳定。
母亲操持家务和人情交往,和伯母很合的来。
姐上学。
我还够不到上学的年龄,每天都由大人抱着牵着去延福门码头。伯父的水果店就在那里。
伯父的生意好。
伯父家有三个男孩,大的跟我姐差不多。
那时,抗战已经胜利,先前的天河街、天河小学,随即刚改名“胜利”。
大人们的日子过的应该是蛮可以的。
南平县解放,好些人打腰鼓,扭秧歌,打钱棍,游旱船。胜利街口就近胜利小学与菜市场之间,搭起一座竹牌坊,杉树枝叶上扎起,披挂彩纸剪成的条。肉市的木柱上,同时还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插着,……这些场景,我倒历历如昨。
那年我足三岁十个月,已经具有记忆能力。七十年来,生平实证了我的记忆力是自己一辈子的较强项。
祖母1950年逝世。我内心中,我们家的最先一段到此。
随后开始的第二段。1953年,我姐去北京上大学,1956年分配到武汉大学任教,1957年结婚。母亲给姐的嫁妆是一条金项链,项链的坠子镶嵌有我姐的一枚极小的照片;还有一件咖啡色方格的无领“布拉吉”。对于姐来说,她有了武大“自己的家”,有了“爱人的老家”,而曾经的我们共同的家,她说成“我爹妈还有我弟弟的家”。
家和我姐之间的联系依靠两种邮件:家书和钱。她上大学时,家里按月寄钱去北京;工作了,她按月从珞珈山寄钱回家,逢年过节和父母亲生日还另外加寄。
这期间,我上小学。
母亲几乎每个月都在数着日子等父亲单位的发饷。
父亲的薪水提升到大约60元时,其中的15元给我姐,15元给我外祖母。
母亲有两次在夜晚跟父亲商量,把两枚金戒指卖了。还说了参加了标会的事。
伯父的家一直租在天河坊,我们也还住胜利街尾。没有了祖母的两家,亲情的密切天天都在联系,几乎没变。
直到四年级时,老大娶亲,伯母去世。那时候,伯父家有五个孩子,全是男的。长嫂代母。
即使1956年我五年级时,我们家搬到梅峰坊,我还是将之归到这个阶段。
第三段,当始于1957年秋,并不因为家搬到梅峰坊,而是我的父母亲借我姐和姐夫暑假回家探亲之末,要他们把我带去武汉,说是“好好读书”。许多年以后,我才晓得是因为我的生父母到从福州到南平来找我。
我的初中、高中都寄宿在校。我说的家,是福建的家,父亲来的信和生活费。我说“我姐的家”,初中时,基本上还每星期来一次回;高中了,就没定期。
1961年伯父病逝。
此间,母亲施行了子宫瘤切除术,而我姐两次流产,第三次怀孕回我们南平的家,由母亲悉心照顾,住院保胎,直到分娩,母子平安。
1964年秋高中毕业后,我回到南平。
第四阶段,1964年秋回家来的我,又和父亲和母亲共住12平米那间。
全家三口,全部的家当包括:父母一床,我夜夜搭铺用的三块长板和四张吃饭凳子;一张吃饭桌和一些碗筷,一个立柜,四只摞起的衣箱,一个木米桶,一张写字桌,一个马桶,一个尿盆。
母亲必须每天操持家务的同时,还得做竹篾的手工编筐,卖给水果店,换到的钱补贴家用。
我的父亲说:“先跟我去仓库,学着点吧!”
唉!现今我七十多了,举目昏花:家的变迁,一曰人口数量,也可以说是人口结构的改变,或因婚姻和出生而多,或因成员变故去而少;二曰住在的迁徙,或异地,或搬移住所。最重要的是安逸。
“安”,安全。“逸”,无烦恼。
而再下去,我们家,不再安逸。包括我姐在“文革”一开始,就胆战心惊地把那条项链交给了党组织:“坚决不要资产阶级的东西”等等。至于我,至于父亲和母亲与我共同命运的家而言,主要的重要的并不是“文革”开始,而是随着我的结婚,我的成家,我的离婚,我的个性的离经叛道。
好想,有个安逸的家。
2018-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