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认识基因的遗传与变异
| | 发布日期:2011年11月18日 来源:春秋农事 原创作者:拾穗居士 点击数: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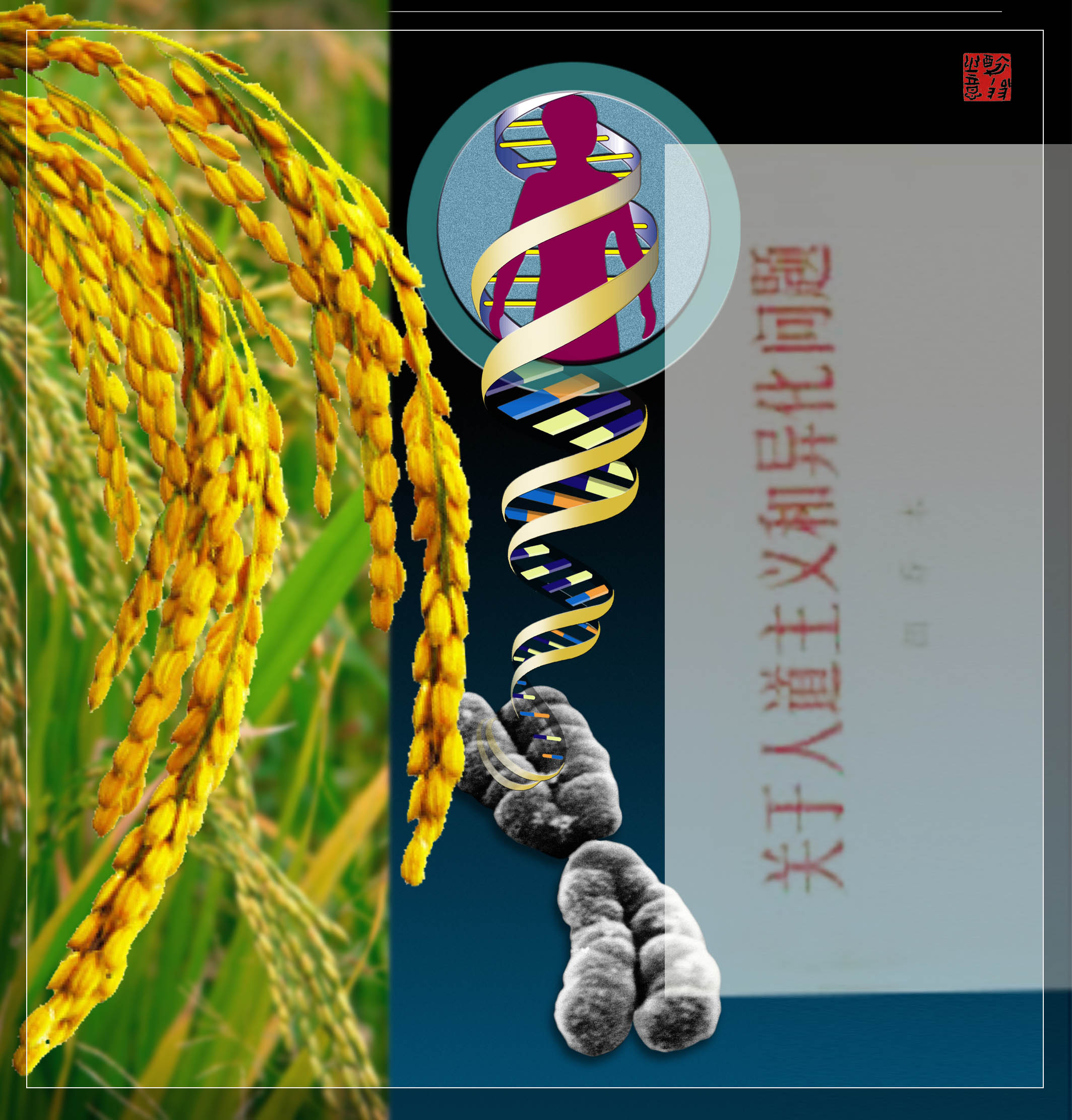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有两门功课讲到基因的遗传和变异,那就是初一学年的《植物学》和初二学年的《动物学》。
这两门功课我学的特别好,每次考试都得满分,而且学起来轻松的很。
《植物学》一开始讲藻类植物、地衣植物、苔藓植物、蕨类植物,它们是不开花,无性生殖,用孢子繁殖后代的孢子植物。植物还有利用根、茎、叶繁殖后代的,营养生殖,例如榕、藕、兰。而人们最常识的,是用种子繁殖的植物,有性生殖。开花,自身授粉,或风和昆虫传授粉,受精,结果。果实本身或果实的内核,即是种子。
“花是植物的生殖器”,那是贾平凹在他的小说里把个赤裸裸说了。搞得我忍俊不止,在大笑中认识了本性。这时候我已是年过半百,有儿有孙之人。
话回过来说,接着是《动物学》。从草履虫说起,它只有一个细胞构成,圆筒形的单细胞原生动物,雌雄同体。后来讲到哺乳动物:“猪的爸爸是黑的,猪的妈妈是白的,它们生下来的还是猪。小猪有的白,有的黑,有的花。生下来的还是猪,这是遗传,出现了花猪,这是变异……”
这是我了解基因遗传与变异最早的知源。
那年代逢大跃进时期,学以致用,能最直接拿到手的遗传和变异之物就是杂交水稻。
现在的人只知道有个袁隆平,岂知袁隆平那时候还不在话下。
这话不能扯下去了,拐过来继续讲基因遗传和变异。
虽然初中的《植物学》、《动物学》,我的考试成绩好,但并不真好。真好要到年过三十,开始能因所学,发现疑点,提出问题,寻找答案的时候。
我二十几岁时找回亲生父母的家,一场同样自幼被抱送别家的和留在本家的兄弟姐妹相认下来,比现在的DNA检测还快还准:一、每个人的后脑勺中间都有“反骨”突出;二、把小的现在照片,与大的过去同龄时期的照片放在一起,相似的程度几近可以完全重叠;三、都不食鱼类、爬藤类蔬果、线面,而喜肉食。后来,又感觉到每个人思维能力都很强,都讲究自我,都极力奋斗,都难得合群,却也都对外义气,而家庭关系都处理不好。如果说我们是同在一个家庭环境成长,那可以解释为“后天”,或者既有“后天”,也有“先天”,然而,实际情况是十胎中,一半被送到外,所余一半,台海异地。因此,我开始思考基因的现象:遗传,遗传什么?变异,什么一成不变?
因为观察自己和熟人,也因为思考和积累,三十多岁时渐渐地我察觉到一个共性的有趣——遗传给下一代的,未必就是父本母本最优秀的基因,而是最突出、最具特征的方面。譬如,父母中有一人高度近视,子女近视;,父母中有一人颧骨暴突,子女亦然;父母中有一人认认真真,另一人马马虎虎,子女马大哈居多。父母学业严重偏科,子女难以幸免……
于是,我回顾初中所学的“遗传总是将最优秀的基因传给下一代”,是否应为“遗传总是将最具个性特征的基因传给下一代”吧?
这点,使得我认可我们家老小初高中考试成绩总不会满分,给予谅解,因为母本做任何一件文字工作时,必有遗误。因为我的谅解,孩子减轻了许多可能令其永不得解的重负。
由此,年过半百后,我开始感伤国民义务教育时期的不幸,其中有一点便是家长不思想自己的本质,不顾忌孩子的本来,父母自己很差,却要求孩子优秀;自己或许优秀,要孩子一定更优秀;既不考虑遗传的基因,也不允许基因往不好的方面变异。
有时,我还会感叹:第一代离乡背井在外大半辈子,生儿育女,照说讲话应该当地化才是啊,怎么绝大多数的第二代还带家乡的口音。这问题,在一次偶然的电视节目里,听台湾诗人席慕容说的,得到启发。她说,自己在台湾生长,几十年从来没回过祖籍,那一年,回来,在蒙古包里学讲蒙语,一出口,就被老乡认可“地地道道”的。她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一位老大爷告诉她,是她还在母亲的胎里的时候,母亲的声音传给了她,叫“母语”。
我联想到台湾已故作家柏杨的人文作品《丑陋的中国人》。一位自称是“野生动物”的先生揭示的民族特质。
之前的鲁迅,在这方面不是写的不够多,阿Q、孔乙己、人血馒头……
1984年1月27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者不是农业专家袁隆平,而是毛泽东秘书之一的胡乔木。胡乔木知道杂交水稻,却在还来不及见过无性繁殖的克隆羊、克隆牛的年代,就死了。据说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因遗产与变异的,我读懂读不懂,待将来,另当别裁。扯政治的干嘛?《植物学》、《动物学》两蛋痛啊!
2011-11-16 上午 穗城





